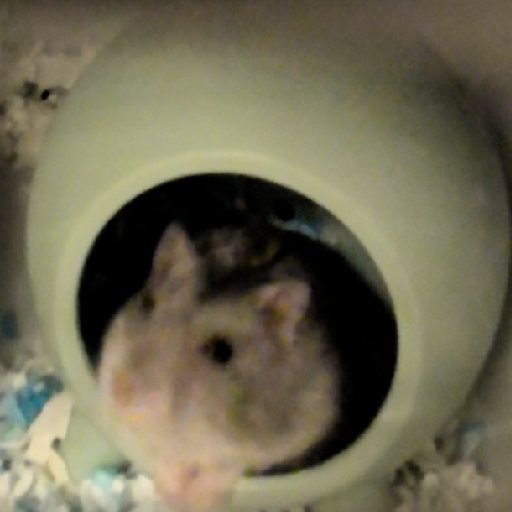第4章:谢文远彻底怒了
乐平县。秋意渐浓。
谢家祠堂的门已经紧闭了三天。
谢清言,这位谢家唯一的嫡女,正被她的父亲关在这里。
“没有我的允许,禁止踏出一步。”
这是谢文远在砸碎了书房的砚台后,对她吼出的最后一句话。
祠堂里很冷。
那种阴冷,是从青石地板下、从那一排排黑漆木的祖宗牌位上渗出来的,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。
空气里,常年飘着一股陈旧的香灰和上好檀木混杂的令人头晕的肃穆气味。
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而言,这里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监牢。
但对现在的谢清言而言,这里很安静,也很自由。
谢清言甚至有闲心去打量那些列祖列宗的牌位,她对这场惩罚毫不在意。
她被关在这里,而她的父亲谢文远,那个急功近利又脆弱不堪的男人,则被关在另一个更大的牢笼里。
清晨,卯时三刻。
谢文远睁开眼,宿醉和郁结让他头痛欲裂。
他坐在床边看着铜镜里那个眼窝深陷的中年男人,眼中满是血丝,不禁回想起以前,他曾经是大周朝元启十五年的二甲第一名,传胪。
何等的意气风发!他曾以为自己会入翰林,进中枢,光耀门楣。
可现实呢?
一纸调令,将他这个天子门生,发配到了这穷乡僻壤的乐平县。
沉浮二十载,分毫不动。
谢文远从一个一腔热血的青年才俊,被这官场活活磨成了一个钻营汲汲的七品芝麻官。
他深吸一口气,穿上了那身青绿色官服。
“老爷,您...用早膳吧。”王氏怯生生地站在门口。
“不吃!”谢文远一把挥开袖子。
当他踏入县衙,踏入那间他主宰了近十年的琴治堂,谢文远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耻辱。
琴治堂是县衙官员日常处理公务,议事的地方。
往日里,这个时辰,堂内总是充满了下属们的寒暄奉承,以及...对他的绝对敬畏。
而今天,堂内死寂。
谢文远踏入高高门槛的那一刻,他听到了压得极低的窃窃私语声——
“......听说了吗?王家那事......”
“......啧啧,卖女求荣......”
“......真是斯文扫地......”
在他脚落地的瞬间,所有的声音,唰地一下全消失了。
那几个平日里最会拍马屁的县丞,主簿,此刻全都低着头,假装在翻阅那些根本看不进去的卷宗。
一个年轻的典吏,刚端起茶杯,看到他手一抖,哐当一声,热茶洒了满手,烫得他龇牙咧嘴,却不敢叫出声来。
谢文远的脸,瞬间铁青起来。
这种安静,比当面唾骂他,更让他难堪。
他能感觉到那些黏在他背后的目光,充满了鄙夷,嘲讽和幸灾乐祸。
坐定位置后,谢文远猛地一拍堂木。
“砰——!”
巨大的声响,让所有人都吓得一哆嗦,齐齐站了起来。
“大...大人......”
谢文远阴冷眼神,缓缓扫过堂内每一个人的脸。
“很闲吗?”
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。
“我问你们!”谢文远猛地拔高声音,“是不是都没事情做了?!”
“大、大人息怒!”
“我等,我等正在处理公务!”
“处理公务?”谢文远抓起手边的一叠卷宗,狠狠砸在那个主簿的脸上,“上个月的秋粮入库表!拖到现在还没给!你就是这么处理公务的?!”
“还有你!”他指向那个洒了茶的典吏,“城南的沟渠修缮款项,你算了三天还没算清!你是猪吗?!”
堂内众人纷纷惶恐跪地,高呼大人息怒。
-----------------
退衙后,谢文远几乎是逃回了谢府,一头扎进了书房。
谢文远研完墨,便开始练字。
在铺开一张上好的宣纸,提起了那支他最爱的紫毫笔。
“忍。”
他想写一个忍字。
可那笔尖落在纸上,却抖得厉害。
他越是想忍,心中的焦虑就越是像潮水一样,将他淹没。
谢文远恐慌两件事。
第一件是卖女求荣。这四个字,像烙铁一样,烙在了他的脸上。他这辈子都别想在乐平县,在同僚面前抬起头来了。
第二件才是真正让他绝望的。他得罪了京城的......王御史。
谢文远的手抖得更厉害了,他烦躁地将纸揉成一团,扔在地上。
他想起了一个月前,王御史的管家,那个比他这个七品县令还要倨傲的奴才,是如何找到他的。
“谢大人,我家老爷,看中你家小姐了。”
“事成之后,谢大人,可调任京城,入王御史门下。”
“入王御史门下...”
沉浮二十载啊!
他这个榜眼,他这个天子门生,在这小小的乐平县,蹉跎了二十年!他已经四十五岁了!再不往上爬,这辈子就真的分毫不动了!
谢文远被那调任京城的诱饵,迷了心窍。
他甚至没去仔细打听,为什么一个三品御史的嫡子,要纡尊降贵,来他这穷乡僻壤和他一个不知名的小县令联姻,他以为这是命运的眷顾,自己要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结果,他那个逆女!
她不仅忤逆他的安排闹绝食闹自杀,还竟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,把这层窗户纸捅了个天翻地覆。
不能人道……
八个活寡妇……
现在,全大周都知道了王家的丑闻!
王御史会怎么想?
王御史会怎么对他?
他不敢想。
那已经不单是名声扫地了,那是家破人亡!
谢文远越想越烦,他心中的悲哀几乎要将他吞噬,心中的愤懑刺向他的神经,太阳穴隐隐作痛。
他猛地一拍桌子,对外吼道,
“来人!”
一个下人连滚带爬地进来,“老......老爷......”
“那个逆女在祠堂如何了?”他咬牙切齿地问。
他希望听到逆女跪地求饶承认错误,然而下人只是惶恐地低着头,如实回答,
“回老爷,大小姐...她很安静。”
“......”
“一日三餐,春草送去,她都吃得一干二净。每日在里面,好像,好像是在抄经练字。”
“砰!”
谢文远将刚换的另一方砚台,也扫到了地上。
“滚!!”
下人又连滚带爬地出去了。
安静?
她凭什么安静?!